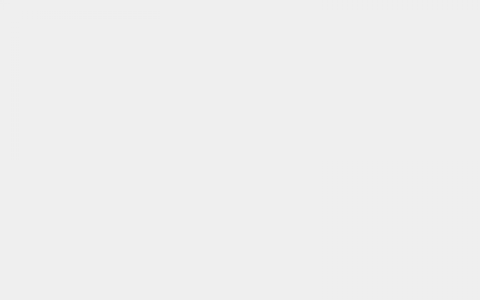我的烟龄已有41年了,每天抽烟都在三包以上,人称“每天起床抽烟,一根火柴到底”的那类。毫不夸张地说,此生,我有两个很少看见:抽烟很少看见有能陪得起我的人,吃饭很少看见有出汗像我这样多的人。
我的烟龄已有41年了,每天抽烟都在三包以上,人称“每天起床抽烟,一根火柴到底”的那类。毫不夸张地说,此生,我有两个很少看见:抽烟很少看见有能陪得起我的人,吃饭很少看见有出汗像我这样多的人。

我开始抽烟,是在1973年3月,未满19岁。由于年轻向上,我被单位选到乡下参加工作队。当时,提倡“四同”即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改造,白天抓生产,晚上闹革命。众多考验中,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被分配到土改根子、贫农小组长家食宿的饥饿。他家一锅照得见人的白米粥,一碗红锅子炒的干辣子,无油无盐,有上碗无下碗,只有清汤寡水、饥肠辘辘,直到现在,想起都饿。
或许是想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,把烟当成联络感情的纽带,又或许是因为饿,总想有点什么到口里打个转。每当乡亲们抽烟时,我就有意无意地凑上去,跟他们要一根,尝尝,然后,就自己节衣缩食买烟抽,见到乡亲们就递上一根。烟不但让我打发了在乡下的寂寞时光,更加深了我跟乡亲们的感情。我也就这样慢慢地“堕落”成一天两包的超级烟民,深刻体会到了从臭到香、由苦到甜的人生烟味。
跟所有烟民一样,我也知道烟的危害,多次想戒,却总经不住烟的诱惑,抽了戒,戒了抽,前后经历了三次痛苦的离合。
第一次是1990年在省委党校学习,同房的朋友刚戒烟不久,一见面,就跟我说起戒烟的种种好处。我清楚他的用意,一时莫名的冲动就宣布戒烟。头三天,夜幕降临,点灯习书,烟瘾来袭,坐卧不宁,只得出门寻烟。几次欲购,几次忍手。经不住香烟的诱惑,就往抽烟人多处挤,贪婪地猛吸“二手烟”。烟香飘来,陡然间,气定神安,是那样亲切,那样美妙!此后,又熬过了5个月,复吸。
第二次戒烟,是1999年。这次戒,应该肯定,比上次准备得充分多了,因为吸烟有害的宣传日盛,新世纪的号角即将吹响,我把戒烟作为挑战自我,给新世纪的一份贺礼,隆重地在工作地较大范围的一个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。可以说,没有给自己留后路。烟戒了,食欲大增,首月增重6公斤。这次戒烟,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的,凡一人独处时,都做到了不思不想不吸一支烟。但每逢朋友聚会时,经不起吆喝,难断“伸手牌”,名曰“吹吹”,实际上是心瘾难除。就这样挣扎缠绵、博弈较量着。10个月后,一个“偶发事件”袭来,令我义愤填膺。朋友来了,关心者来了,当然“烟伙计”也关怀备至地来了。此刻,与它的亲仇,都显得是那样的无足轻重。自此又功亏一篑。
那么,这第三次戒烟,又是因何而起呢?
4年前,慈母因肺癌辞世,对我打击很大。母亲,长沙人,1950年初,带着襁褓中的大姐,与父亲一道进入湘西参加地方建设。在湘西,她先后生下了哥哥和我,还有两个妹妹,加上姐姐,就是姊妹5个。她克己待人、节衣缩食、任劳任怨、相夫教子,用瘦小病弱的身躯,担当起一大家的重担。在“文革”中,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下放到湘西高山台地———腊尔山劳动改造,姐姐下放到洞庭湖当知青,哥哥下放至外婆的老家当知青,我在休学一年后,被录取到被称为吉首偏远的丹青公社中学初中部就读,小妹寄养在舅舅家里。一家人各自东西,母亲把一颗心掰成多瓣,把爱撒向四面八方。
母亲就在这时也开始学会了抽烟。那时道路不畅,没有电话,孤独的母亲,只能把对亲人们的思念点成一支烟,一缕一缕飘向夜空,飘向亲人。
2011年,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主要致病原因是长期抽烟。3个月后,她与世长辞!
母亲过世后,像年轻人一样青春不老、喜欢唱歌跳舞的父亲,突然腰不能直、腿不能迈,成天瘫坐在沙发上,郁郁寡欢,魂不守舍,瞬间苍老了许多,几年后,随母而去。
父母之死,与烟有关,与悲伤有关,与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有关。可能是过多沉陷在悲痛中,他们的死,没有让我与戒烟联系起来,真正促成我戒烟的是一位朋友。
去年中秋,我和妻子赴京看望儿女。当时瓢泼大雨,交通中断,我们滞留在火车站。这时,接到朋友妻的一个电话,告知朋友已住院,初步诊断为肺癌。这位朋友,与我共事多年,志趣相投,情同手足,平常身体健康,每年体检是他最骄傲的时候。接到电话,我二话没说,退票直奔医院。手术下来,五叶肺割去一叶,所幸的是尚处早期。
看来,这一次我真的要痛下决心戒烟了!理由无它,为了健康地活着!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,发布者:实习编辑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dbykq888.com/jieyangushi/1870.htm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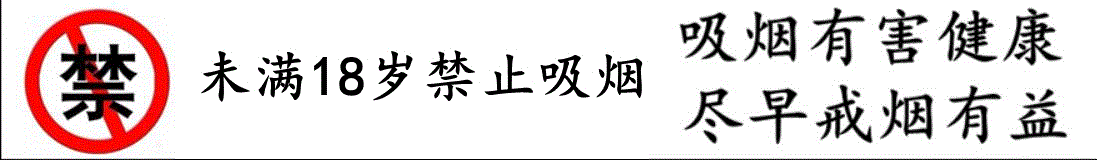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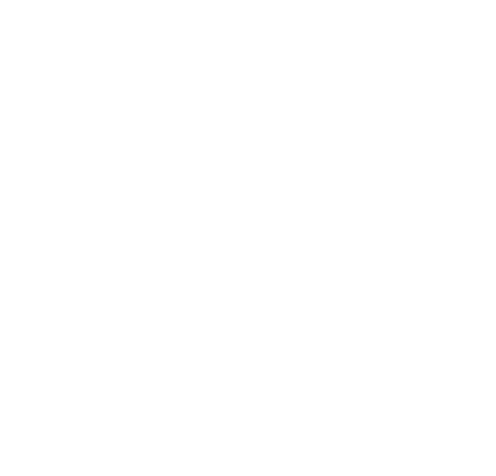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